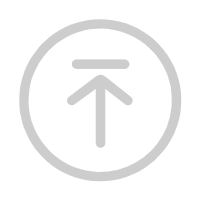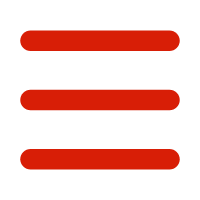2019年6月6日星期三15:00,日语系在第二教学楼221室举行了以“聆听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声音(日本文学を<聞く>)”为题的讲座。主讲人是来自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日语语言文学系的副教授——山本幸正老师。本次讲座由日语系尹松老师主持,日语系1-3年级同学以及尤海燕老师、金晶老师、杨敬老师、外教岛田老师到场参加。

山本老师不仅学识丰富,而且幽默风趣,充满活力。在简短的自我介绍后,山本老师提出了几个问题:去过日本的同学,你们觉得中日两国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?同学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——比如觉得日本的厕所很干净。而对于山本老师而言,中日最大的区别则在于“声音”。众所周知,中国是一个“热闹”的国家,不论是餐馆还是地铁中,都能听到各种声音;而日本则是一个“安静”的国家,尤其是公共场所,没有人大声喧哗,车也不会鸣笛……似乎日本人更加喜静。但山本老师恰恰相反——他喜欢充满声音的地方。因此他住在东京最热闹的街道上,因此他来到了中国,也因此他开始注意到“声音”的魅力——就连文学作品中,都充满了声音。

说起声音,一定会先想到音乐。在日语中,“听音乐”的听用的汉字不是“聞”而是“聴”,这是为什么呢?两个“听”表达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吗?山本老师首先从这两个异字同训词入手,为同学们讲解了“听”的含义——“聴”表现的是一种有意识地排除杂音的聆听,而“聞”则是无意识的、甚至有些被动的听。而且和“看”相比,当我们不想看某样东西时,我们可以选择闭上眼——但我们却很难阻止不想听见的声音进入耳朵。回忆一下每天早上叫醒你的闹钟——它并不是通过视觉,而是通过听觉唤醒你的,不是吗。所以说,“听”这个行为中还存在一定的被动性。因此,哪怕是一些不怎么优美的杂音,我们也不得不去听他们。但是,杂音为什么不能称为音乐呢?——上世纪的音乐界终于开始了对“听杂音”的摸索,也诞生了《4’33》这样,在音乐厅中留出大段空白,让听众感受身边的杂音的作品。古时候的日本,其实是不太区分“楽音”和“騷音”的——直到西欧音乐进入日本,日本才开始对这二者进行区分。而且,其实各种文化中对“騷音”的感知也不尽相同——就拿虫鸣声来说,有的文化中,“赏虫鸣”是风雅闲适之事,而有的文化中却认为虫鸣聒噪难闻。

第一小节“音楽の<現代性>とは”就深深地吸引住了同学们,而第二小节的“<現代性>を体現した日本の作曲家”和第三小节的“日本文学を<聞く>”更是仿佛为同学们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。首先,山本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日本作曲家武满彻。武满彻创作个性鲜明,音乐语言新颖独特,在日本音调基础上运用了西方现代音乐技法。其音乐受多方面影响,如具体音乐和电子音乐,德彪西和梅西安的风格等。他作有大量电影配乐,与黑泽明等日本电影大师都有合作。本次讲座中,主要涉及了武满彻的具体音乐作品。具体音乐是将来自自然界、环境声源,通过麦克风录制后剪辑、变速、声音异化、电子加工等操作后固定下的作品,也就是将音乐概念扩大到自然音响中。在中国,谭盾可以成为具体音乐的代表人物了。山本老师带领同学们欣赏了武满彻的具体音乐作品和谭盾的《水乐》,《纸乐》。新奇的乐声深深吸引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
那么,在文学作品中又有怎样的声音呢?在日本近代文学中,通过“眼”来捕捉已经不足以表达了,“耳”的功能也日渐重要了起来。山本老师选取了国木田独步的经典作品《武蔵野》中一段声音描写。风声、鸟鸣、脚步、人声……一个短暂的场景中竟然可以捕捉到如此之多的声音。比如在正冈子规(夏目漱石的好友)的俳句中,就可以看到许多声音的描写。在俳句中,表达“推量、推定”含义的有两个语法,分别是“めり”和“なり”。前者的“めり”指的就是“目”,眼睛;而后者是通过耳朵。正冈子规的作品中所用的“なり”,正是由耳捕捉到的信息。再看到太宰治作品中的“トカトントン”,也是文学作品中经典的“声音片段”。山本老师用落语般的感觉为同学们读了一遍“トカトントン”的段落,生动地展现了“トカトントン”段落中隐含的“リズム感”——虽然一整段只有一个句号,却因为有了“トカトントン”划分句子而不显得冗长,反而充满了节奏感。

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中,有同学问“黄色い声”中,为什么可以用黄色描写声音。山本老师从语源为同学进行了讲解。最后进行了合影留念。

不到两个小时的讲座中,山本老师妙语连珠,带领同学们聆听了文学作品中的声音。这是一场全新的体验。希望通过本次讲座,能为同学们打开看待文学和看待世界的新思路。
撰稿:李佳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