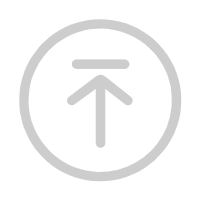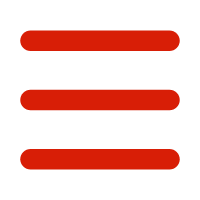生平:罗玉君(1907—1987),原名正淑,文学翻译家,四川岳池人,中国民主同盟盟员。1933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,先后但任过山东大学、华西大学、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教授。1951年起,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。生于四川岳池县的罗玉君,读小学时就显示了过人的见识和写作才华。12岁那年,她参加全县的小学生作文比赛,比赛题目是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论》,罗玉君的作文立论准确、说理缜密,还具有朴素的民主思想,当之无愧地获得第一名,成为闻名遐迩的“女状元”。她在重庆考入第二女子师范学校,后来又考入上海大夏大学,提前毕业后,去法国巴黎大学留学。她在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雨果、巴尔扎克、乔治·桑等人的作品。罗玉君在巴黎巧遇自己在重庆读书时的老师李珩,后者正在法国学习数学、天文,并取得天文学博士学位,后来成为我国著名天文学家。罗玉君与李珩在巴黎结婚生女后,1933年回国工作。罗玉君作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最年轻的女教授,授课之余,开始翻译《红与黑》,“工程量”虽浩大,她的译文却做到了信、达、雅兼具。上世纪50年代,她又重译全书,该书深受好评,久印不衰,发行量累计达数十万册。罗玉君译著极丰,不少译本多次选入大学教材。她80年代翻译出版的《海上劳工》《红屋骑士》等长篇小说,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。


代表作品:被称为“女翻译家中的佼佼者”的罗玉君,擅长翻译以心理分析见长的作品,譬如都德《阿里女郎》、聂芳《母爱与妻爱》、柏乐尔《青鸟》、莫泊桑《我们的心》、乔治·桑《魔沼》、司汤达《红与黑》、雨果《海上劳工》、比·加玛拉《自由的玫瑰》、大仲马《红屋骑士》等。她还撰有《论海涅》《论雨果》《歌德与浮士德》和《论司汤达的(红与黑)》等论著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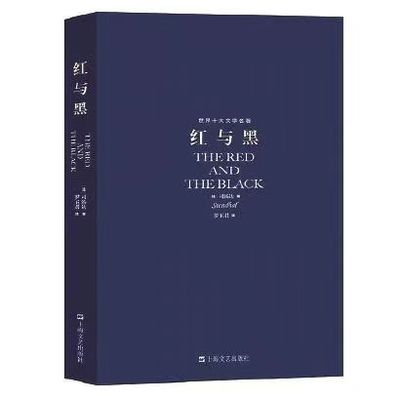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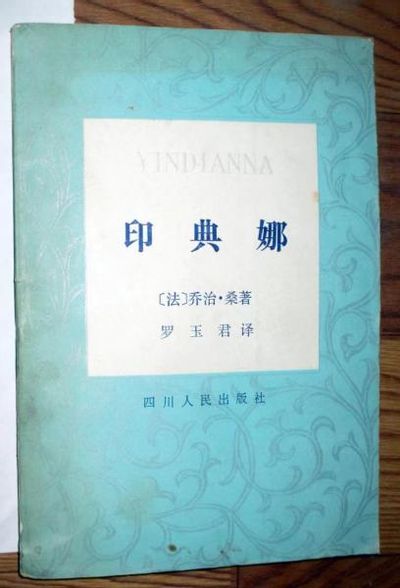
翻译故事:《红与黑》是19世纪法国第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杰作,对19世纪欧洲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罗玉君早在1932年与《红与黑》结缘。她当时在法国巴黎大学,为了文学预读心理分析学,听从乔治杜马先生的建议,买来经典作家集版《红与黑》上下册,热情地读了起来。罗玉君读了一遍后,便有意把它翻译成中文。因当时忙于写博士毕业论文,她只译了五六章,翻译工作就搁置了。1933年罗玉君到青岛后,又着手开始翻译《红与黑》。她曾这样回忆:“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我结婚,一九三三年我回国,定居在绿油油的青岛后,我又才重理旧业。那时我在山东大学教课之暇,总是临窗伏案,做这种翻译工作。不料七七事变起了,卢沟桥的炮声,不但毁灭了我们青岛理想的乐园,也打断了我的《红与黑》译本的繁华的梦幻。”
抗战期间,罗玉君在迁徙流离中,一直把《红与黑》的译稿带在身边,经过数年的努力,终于在1947年夏天全部翻译完毕。1948年夏天,她又进行了全文的校对与部分的抄写。罗玉君曾回忆说:“今年暑假,成都多难。在米荒水灾之中,我一直与《红与黑》做着好朋友。每天写得腰酸,写得手软,写得朵朵的黑云,从我眼底飞来飞去。但是我决心要把这个难产的孩子哺育成人……我不敢说我的《红与黑》是名作名译。但是这译本的工作,经过了我的少女时期,少妇时期,它的年龄比我的长女还大三岁。这不能不算是我的生活史上的一个纪程碑。因此我珍重这译本。”
罗玉君的《红与黑》译本,1949年由正中书局出版,至今仍不断出版,发行量多达数十万册,深受广大读者喜爱。“她的译文不仅保留了原作人物的语言个性,而且较好地保留了原作的鲜明节奏。此书的翻译奠定了她在法国文学翻译上的地位。”赵瑞蕻评价罗玉君的译本“译笔生动流畅,在我国普及《红与黑》这本杰作方面,罗女士做出了贡献”。